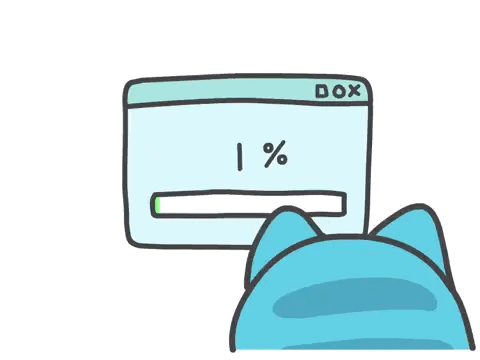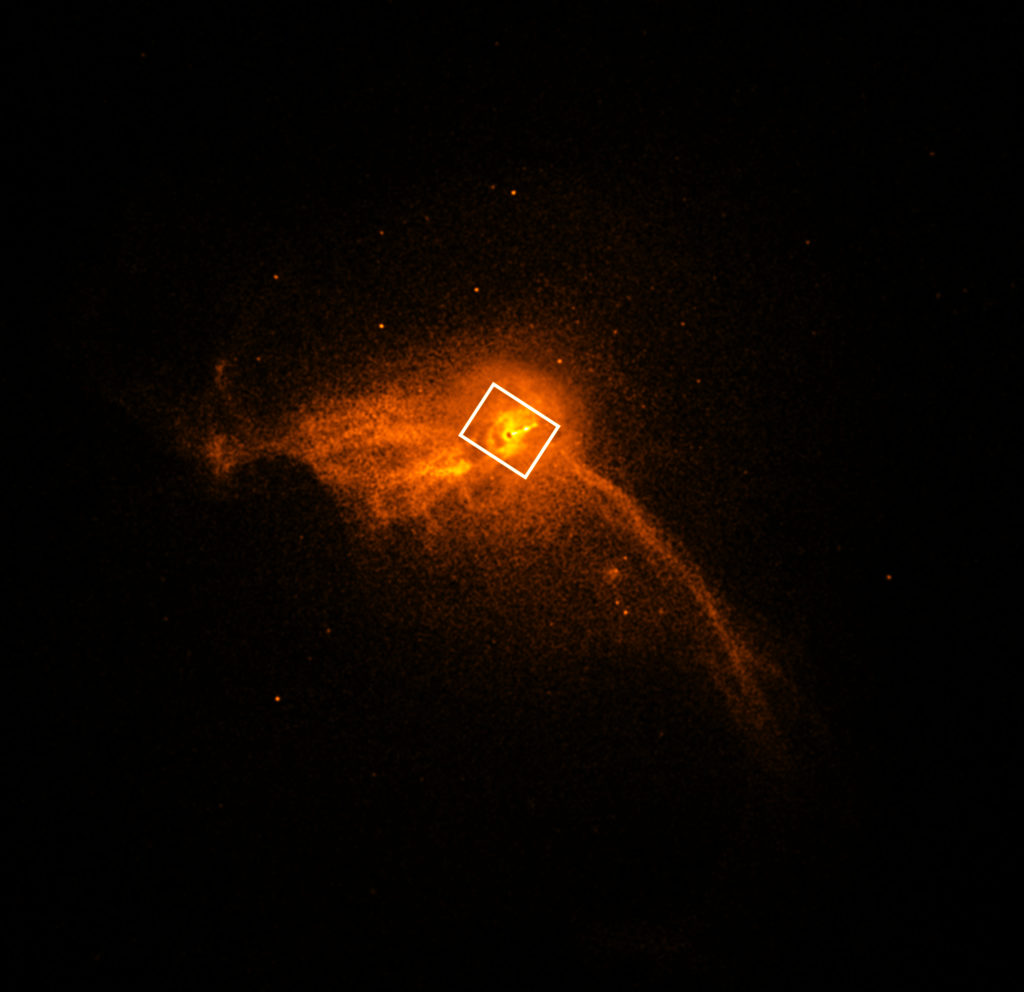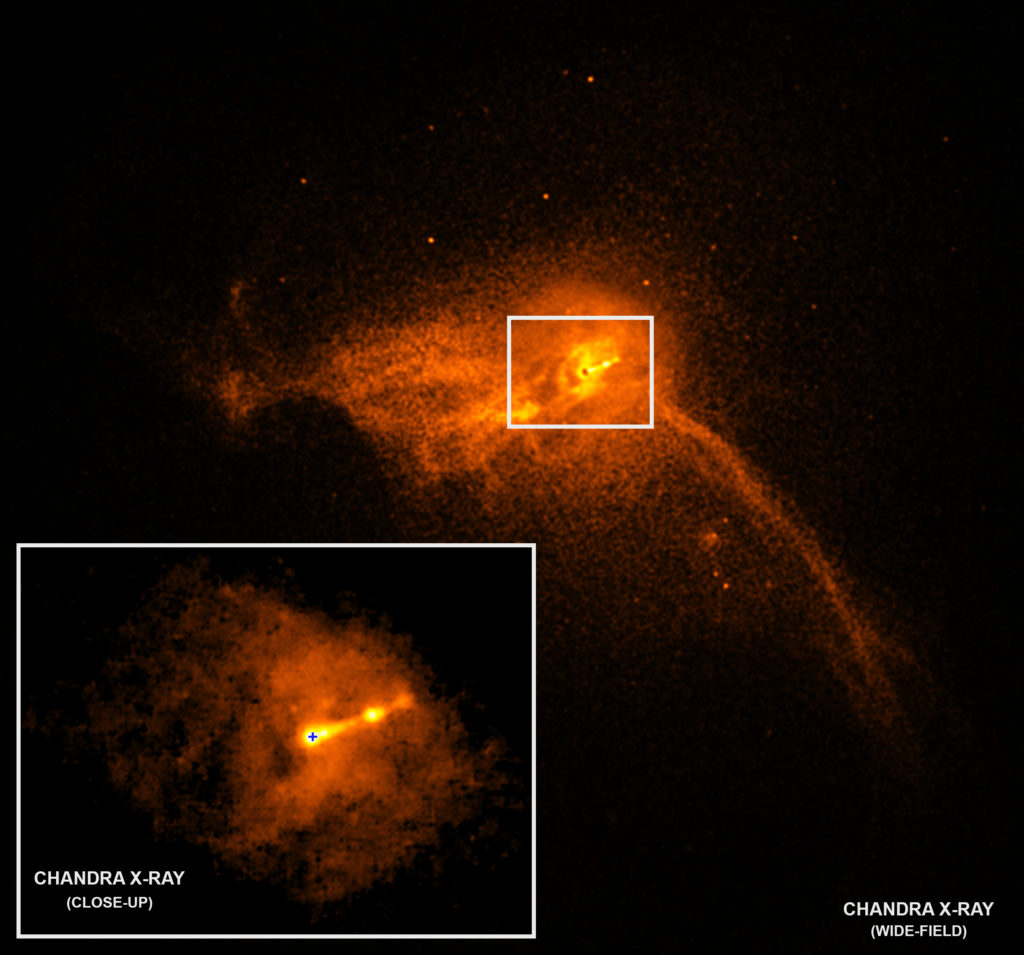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华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所
李卓 吴景淳 裴端卿
自 DNA 双螺旋结构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被克里克和沃森发现,相继研究导致“中心法则”的诞生, 生命科学就开始了空前的高速发展。每隔三五年便有重大发现问世,由此重塑了人们对生命的认知。在不足七十年的时间,这些发现和发明为人们探索生命奥秘点亮了无数里程碑式的灯塔,也极大丰富了人类的智慧。基因编辑就是这些无数灯塔之一, 或许是最耀眼的。人们试图用最原始的办法,例如育种来改变作物的形状,以提供更好的食物。但基于 CRISPR 的方法改变了游戏规则,使这一过程极简单又精准。就目前的进展来看,基于 CRISPR 的基因编辑高效精准、简单易用、成本低廉,产生了许多以前认为不可能的新应用,也让外科手术式的基因改造进入了可以普适性运用的年代。
在 CRISPR 发明之前,已经有 ZFN 技术可以用来做类似精准的基因编辑,但使用起来极其繁琐、昂贵。随后,TALEN 技术的发明改变了这一点, 使基因编辑变得简单和便利一些。但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迭代使得 CRISPR 已成为生物学中自重组
DNA 诞生以来最具突破性的工具之一,因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已经并不局限于学术界, 更进入到了公众视野。人们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开始议论它,并对它之于人类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无限的畅想。这其中有对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对自身及世界更深入理解的工具的欢喜与兴奋,也包含了这些技术可能被用于突破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的恐惧。尤其是使用CRISPR/Cas9 操作人类胚胎的第一份报道发表后,更加深了各种情绪的碰撞, 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于该技术在编辑人类基因组中潜在的应用的争论。这些情绪最终化为了行动,促成了由中、美、英三国 4 家最高级学术团体组织,并于 2015 年 12 月举行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峰会成功举行后,由 22 位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深入研究了解人类基因组编辑的科学、伦理和监管。由此产生的报告建议继续支持基础研究,通过基因组编辑的新颖应用来探索生物学的新视野,以产生先前无法实现的知识,例如早期人类胚胎发育。报告强调了体细胞基因组编辑作为一种治疗工具预先存在监管框架的重要性,同时承认在治疗 ( 维持或恢复特定的功能 ) 和改善 ( 超出个人最初预期的功能 ) 之间划清界限的困难。然而,超越了此前的类似的论述,报告为处理可遗传的基因组编辑提供了一种宽容而非常谨慎的态度。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在有限的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情况下,进行可遗传的编辑在道德上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允许的。总体而言,这些准则是一套明确的原则,任何希望从事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国家都应该采用这一原则。除此之外,报告还强烈建议社会各界参与相关政策的讨论,以及就什么是符合伦理道德但超出了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限制范围的问题达成具有共识性的一致。自报告公布以来,已经在科学和大众媒体上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引用。本文将简要讨论基因编辑的科学性、临床应用、伦理与监管。
修正遗传突变、罕见病治疗与人类胚胎学发展的前景
基于其高度精准的特征,CRISPR 的运用从理论上讲,可以修正任何遗传疾病的病因 ——突变, 从而达到疾病治疗的效果。 其具体运用可以分为体细胞基因编辑和胚胎基因编辑,前者是不可遗传的, 后者如果能成功将会遗传给后代。Ma 等报道了在植入前人类胚胎中纠正了 MYBPC3 基因 ( 一种与显性肥厚型心肌病相关的基因之一 ) 中的四碱基 GAGT 缺失。与以前的报道不同,这项新研究不仅使用了二倍体人类胚胎,而且还宣称提高了效率、准确性和减少了嵌合,从而为这种方法的临床应用开辟了新的基础。通过胞质内注射将 Cas9 蛋白和精子引入 M 期卵母细胞中,他们宣称嵌合体大幅减少并获得更有效的同源定向修复。然而,作者提醒说,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证明其对于其他类型突变 ( 例如碱基替换和更大片段的 DNA 删除、复制和回复 ) 的可重复性和普遍性。尽管他们的研究取得了成果,但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对杂合突变的校正,因为修复显然依赖于同源的野生型拷贝,即母体等位基因,而不是合成的 DNA 模板。另一方面, 根据动物研究和人类胚胎的初步报道,CRISPR/Cas9 直接注射到受精卵中时,很难避免嵌合现象。不是胚胎的每一个细胞都必然携带所需的遗传改变,而且可能会在目标位点引入其他种类的突变。显然,这一研究还处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也备受领域同行质疑。
胚胎水平的基因编辑临床应用,最大的受益方便是潜在的遗传性罕见病患者。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是罕见病并不罕见,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据估计,我国每年有 90~100 万缺陷患儿出生,约占出生总人口的 5.6%,已严重影响我国出生人口素质和儿童健康水平。胚胎基因编辑是治疗严重遗传性疾病最有效、最直接、最根本的治疗策略。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组精确操作, 不仅可以让带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高危个体顺利出生,使其自身终生摆脱该种遗传疾病,还可以将纠正后的正确基因序列传递给后代,让后代也尽可能地避免患上此种遗传病。与优生学目的不同,目前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诸如地中海贫血症、亨廷顿舞蹈症、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血友病等对人类健康有重大威胁,并且尚无有效治疗方案的疾病。现在大的趋势是乐观的,在涉足基因治疗领域的制药公司、生物医药初创企业的研发投入上,除肿瘤癌症类外,遗传病获得了最多的研究资源和经费。
虽然人类基因组编辑报告中规定了严格的许可前置条件,但从技术上讲,目前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对人类疾病进行可遗传基因编辑。当然为了达到有效和无风险的目标,必须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来填补知识的空白。自该报告发布以来,脱靶效应和嵌合现象再次引起关注。鉴于人们对该系统的理解以及世界各地科学家的应用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前者应该在短期内可以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尽管人类胚胎的突变校正可能会继续占据媒体的头条,但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也为理解早期人类发育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正如报告中所预期的那样。英国和瑞典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 如 NPR 和卫报的报道 )。生物学中最令人着迷的问题之一是受精卵如何形成构成人类的不同细胞类型。在小鼠和其他物种中进行的工作为胚胎发育和多能性起源提供了概念性框架。然而,小鼠和人类胚胎发育的分子细节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可能在它们衍生的干细胞中出现。更好地了解早期人类胚胎的遗传回路将有助于寻找真正的“naïve”人类多能干细胞。此外,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可以帮助探索早期妊娠丢失和植入缺陷的遗传基础,特别是如果结合最近改进的人类囊胚培养方法。根据英国、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的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范,科学家只允许培养人类胚胎至 14 d。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基因编辑也可以提供对植入后发育早期阶段 ( 包括最早阶段 ) 事件的深入了解。然而,将该规则延伸至 14 d 以上将开辟人原肠胚形成、胚层形成和体外生殖细胞发育等方面的研究, 否则人类发育的各阶段是无法获得全面研究的。
技术: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挑战
2018 年 7 月,英国 Sanger 研究所的 Kosicki 等发表了他们使用第三代测序技术获得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sgRNA 作用的靶点附近会产生基因组大段的缺失。由于第三代测序技术读长更长,因此可以捕获到基因组的大段缺失以及染色体易位,而这类基因组事件的检测是第二代测序技术不能胜任的。他们的结果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于已有研究由于没有采取恰当的检测技术而得出了不恰当结论的怀疑。
正如人类基因编辑报告所预期的,无论目前已有研究的结论是否恰当,这些研究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并激发研究人员针对具体的问题寻求恰当的检测方法。与通常的科学进展一致,目前已有一些建议提出对近几年中关键性的某些研究进行额外的实验,以证实或澄清观察结果及其背后的机制,并最终进一步促进对报告中列出的原则进行改进。
此外,CRISPR 系统来源于细菌,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体内并没有 CRISPR 系统及相似蛋白的存在,但人体内却存在针对 Cas9 蛋白的免疫应答机制。因此,在确保向人体或人类胚胎中引入外源 CRISPR 系统有效的同时,又不引起机体的强烈免疫应答,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外源 CRISPR 是否会对细胞或组织器官造成基因组之外的影响仍然缺少研究,特别是 2018 年 CRISPR/Cas9 与 p53 基因互有促进及抑制的报道,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目前来看,并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可以将所有sgRNA 靶点区域出现的事件清晰地描绘出来,而对于更高维度的细胞、组织,甚至个体本身的影响依然缺乏有效的评估。因此,基于现有技术的“鸡尾酒式”的检测,以及针对性的新技术开发,从而确立基因编辑安全性与有效性的“金标准”,在未来研究的日程表上显得尤其突出。
另一种提高安全性的策略是针对特定问题提出替代解决方案。单碱基编辑技术便属于此种情形。众所周知,大部分的致病性 DNA 异样为单碱基突变,而采用切割 DNA 双链纠正单碱基的策略,不但会导致纠正的效率不可控,而且位于被切割区域的染色体易位、碱基的丢失与插入、大片段 DNA 的丢失与插入等诸多意想不到事件的发生也是不可控的。而单碱基编辑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仅使用 Cas9 或 Cpf1 蛋白的定位功能 ( 或伴随使用 DNA 单链切割功能 ),将融合表达的碱基作用结构域引导到基因组特定的位点,并对该区域内的特定碱基进行突变。目前已经可以编辑的碱基包括 C>T 和A>G ,而采用将碱基作用结构域与具有更广泛识别 PAM 的 xCas9 或 SpCas9-NG 结合的策略, 更可以将可执行纠正操作的致病型单碱基突变扩大至数千个。单碱基编辑的策略极大地扩展了对致病型突变的干预能力,而且因其不会主动切断双链DNA 而具备较高的安全性,因此,这项技术在基因治疗领域引起了极大的乐观情绪。
伦理与监管挑战
目前在使用人类胚胎作为研究对象的国际规则和法规上存在着分歧,尽管在人类胚胎中进行体外基因组编辑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发现有关人类发育的宝贵知识。人类基因组编辑报告认为,可遗传的编辑是合乎道德的,但前提是必须符合严格的前置条件。这些前置条件包括在现有条件下没有合理的替代方案来预防严重的发育、生理缺陷,且存在强有力的监管力量以监督实施方案设计、执行以及长期的后续行动。
在衡量一项可遗传编辑的应用时,应当采纳适当的原则在风险与收益方面进行合适的评估。因此, 即使某项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编辑在特定管辖区域内获得了许可并合法开展,也希望该区域的监管部门在批准之前采用这些准则。现在的问题是,监管机构是否准备好接受这样的申请、审查及批准。因为, 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可遗传的编辑是合乎伦理的,但这是否是一项基本权利似乎是不明确的。
就像所有的新科学一样,公众对人类基因组编辑前景的期望和焦虑程度都很高。人们对优生学的恐惧和对“扮演上帝”的担忧加剧了这些反应,这在所有社会中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文化和历史根源。应该听取和考虑这些合理的关切,并且必须进行公开讨论。
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国际讨论应该审视各司法管辖区不断发展的监管框架,以期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一些共同的原则。合作开发合适的公共讨论的参与方式,以帮助在可接受的基因编辑的伦理界限上作出决策,以此为主要目标,使社会、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跨国多样性成为一种推动力,而不是成为达成进一步共识的障碍。此外,国际协议应该在这一重要领域促进开放科学,并解决与国籍、知识产权和商业利益有关的任何障碍。
国际峰会组织者呼吁建立一个持续的国际论坛,继续讨论基因编辑的人类临床应用。跨国合作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建议的七项原则之一。需要高层次和持久的合作,以解决报告中确认的关键问题。例如,在可遗传基因编辑被考虑进行临床试验之前,国际合作可以通过使用人类和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帮助解决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机会获取人类或非人灵长类胚胎,这取决于当地的监管和成本问题。因此,一项精心设计和拟订的合作协议将使工作能够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在财务上可行,在后勤上可管理,并且能够汇集最终的知识,以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形成满足各个国家监管机构要求的证据。
人类基础生物学的跨国合作可能是最紧迫的问题。正如报告中指出的,人类胚胎的编辑代表了一个更好地了解早期人类发育的独特机会。虽然现在已经有几个实验室已经开始或计划开始研究人类胚胎编辑的方法,但仍需要协调一致的努力。首先, 个别研究者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完成所需的所有工作尚不清楚。其次,鉴于人类胚胎作为研究材料的政策分歧,特别是专门为研究而创造的胚胎,许多合格的科学家可能不被允许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第三,人类卵母细胞和胚胎是稀缺的,许多研究人员可能无法获得。最后,几个实验室可能正在研究相同或非常相似的问题,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重复, 浪费宝贵的资源,造成不健康的竞争。一个国际合作机构,例如一个大学联合体或科研联盟,可允许共同处理一些有趣的问题,并且可以生成、分析和共享数据。关键的是,一个联合体将能够制定详细的指导方针,使科学界能够在各自的国家中遵循和实施。一个高效合作的联盟将能够专注于 4 个目标: 利用特定调控网络标注的细胞谱系生成一个完整的早期人类胚胎发育地图 ;从受精卵到原肠胚生成一个详细的单细胞人类细胞图谱 ( 基因表达、染色质结构等 ) ;建立与特定发育或临床异常相关的人类基因组变异的相关数据库 ;并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强大的工具和资源平台,以从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角度来理解人类发展。在这些资源可用的国家,这些研究应该与非人灵长类胚胎的研究相辅相成,扩充灵长类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的知识基础。
人类基因组编辑工作进展迅速,在第一届峰会成功召开之后,有大量学术研究论文发表,人类基因编辑在各方面所呈现出的问题均需要与时俱进的讨论,因此,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顺势而生。第二届国际峰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于香港召开, 本次峰会将继续讨论医学应用的相关问题,以及针对基因编辑技术本身的学术讨论,并将就第一届峰会后发表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详尽的探讨。
基因编辑技术为人类健康带来了全新的图景,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项技术能为生物学的基本理解带来巨大机遇,特别是早期人类胚胎的发育。我们由衷地期望通过利用峰会发布的原则和建议,设计并建立一个包括全球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国际合作环境与机制,从而使基因组编辑可以在医学和生物学上透明、高效,以及具有人文关怀地实现最大效能,以此服务人类社会。